自由的使命:让他人也获得自由
创建于:2025年8月10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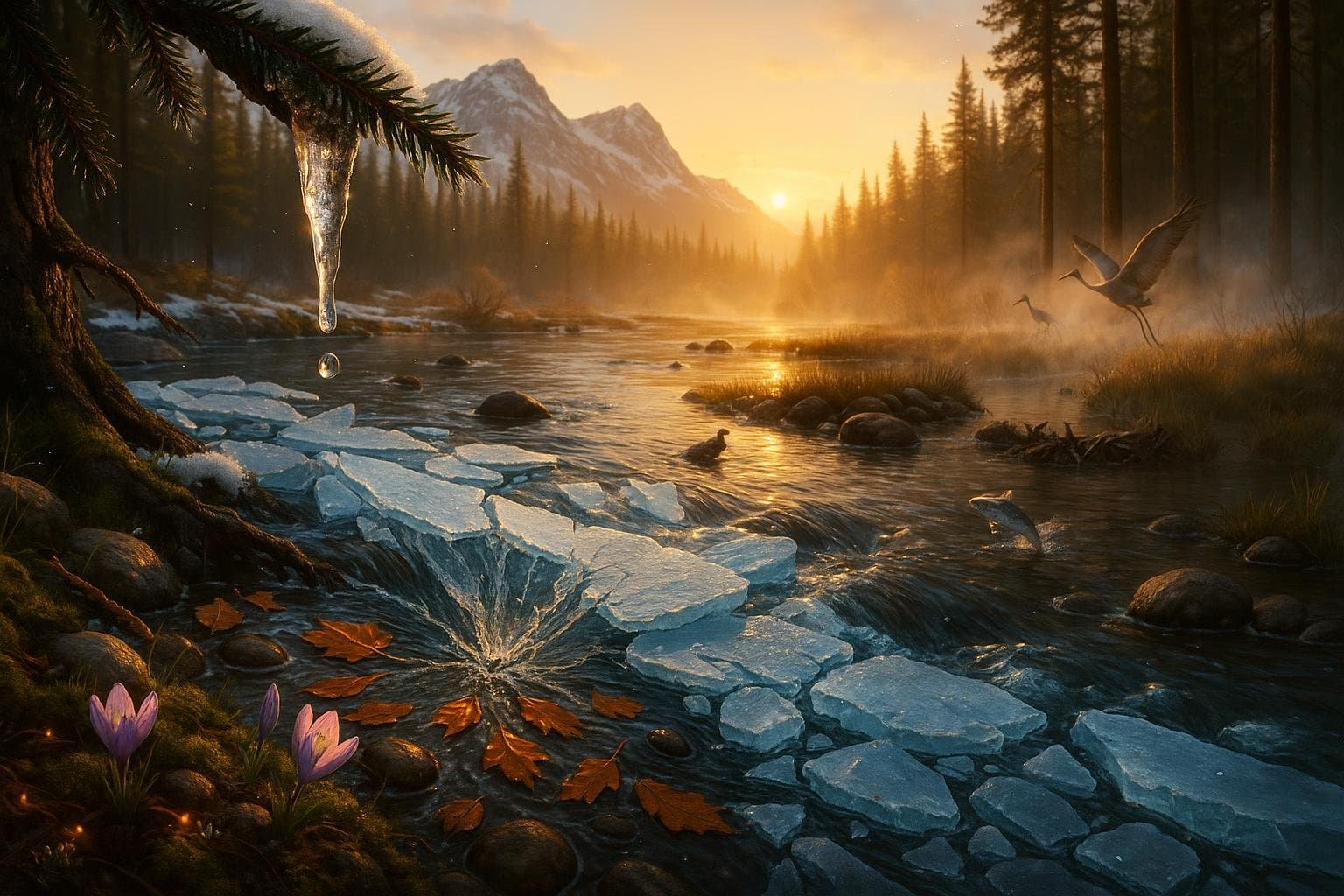
自由的功能就是让他人自由。——托妮·莫里森
自由的连带责任
起初,莫里森的断言把“自由”从一种私人感受转化为公共职责:它的功能,不在自我占有,而在向外辐射。换言之,个人的解放若不能成为他人获得可能性的通道,便仍未完成。从这层意义上看,自由像火种,唯有不断点燃他者,才能成为持续的光源,而非转瞬即逝的火花。
历史回声与公共行动
顺着这条线索,历史提醒我们:自由一旦被组织起来,便从个人美德过渡为公共工程。马丁·路德·金《伯明翰狱中来信》(1963) 指出正义的相互联结,说明个体的安全感离不开共同体的解困。由此,投身废奴、民权、女权与劳工运动的人们,将私人的觉醒转换为制度性推进,让自由成为共享的现实。
莫里森文本中的解放实践
回到莫里森自身的写作,《宠儿》(1987) 以创伤与记忆追索自由的代价,而《所罗门之歌》(1977) 则以“飞翔”的母题召唤代际的解缚。这些叙事不止于个体创痛,更强调社区的相互扶持如何使人重获主体性。同时,她在兰登书屋的编辑实践,推动众多黑人作者进入主流,也是在出版生态中兑现“让他人自由”的职业路径。
语言与教育的解放力量
进一步说,通往自由的工具常从语言与教育展开。保罗·弗莱雷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(1970) 主张以对话唤醒被压迫者的能动性;莫里森在诺贝尔演讲(1993) 亦强调语言既可桎梏也能解放,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讲述与倾听。因此,培养叙事权与解释权,便成为把自由传递给他人的首要技艺。
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
因此,在概念层面也需转换视角。以赛亚·伯林《两种自由概念》(1958) 区分免受干预的“消极自由”与实现能力的“积极自由”。莫里森的命题更接近后者——不仅拒绝压迫,也要建设条件,使他人有能力选择与行动。呼应阿伦特《论革命》(1963) 对公共行动的强调,自由最终要在共同的世界中被实践与维持。
把信念落地为制度与日常
最后,使命需落地为方法:在制度层面,推动投票权、教育与住房机会、数据与劳动保障,使自由可被获得和维持;在组织与日常中,通过导师制、资源共享、无障碍与反歧视流程,让他人的潜能得以伸展。正如密尔《论自由》(1859) 的伤害原则所示,自由与责任相依相生;当我们为他者扫清障碍,也是在巩固彼此的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