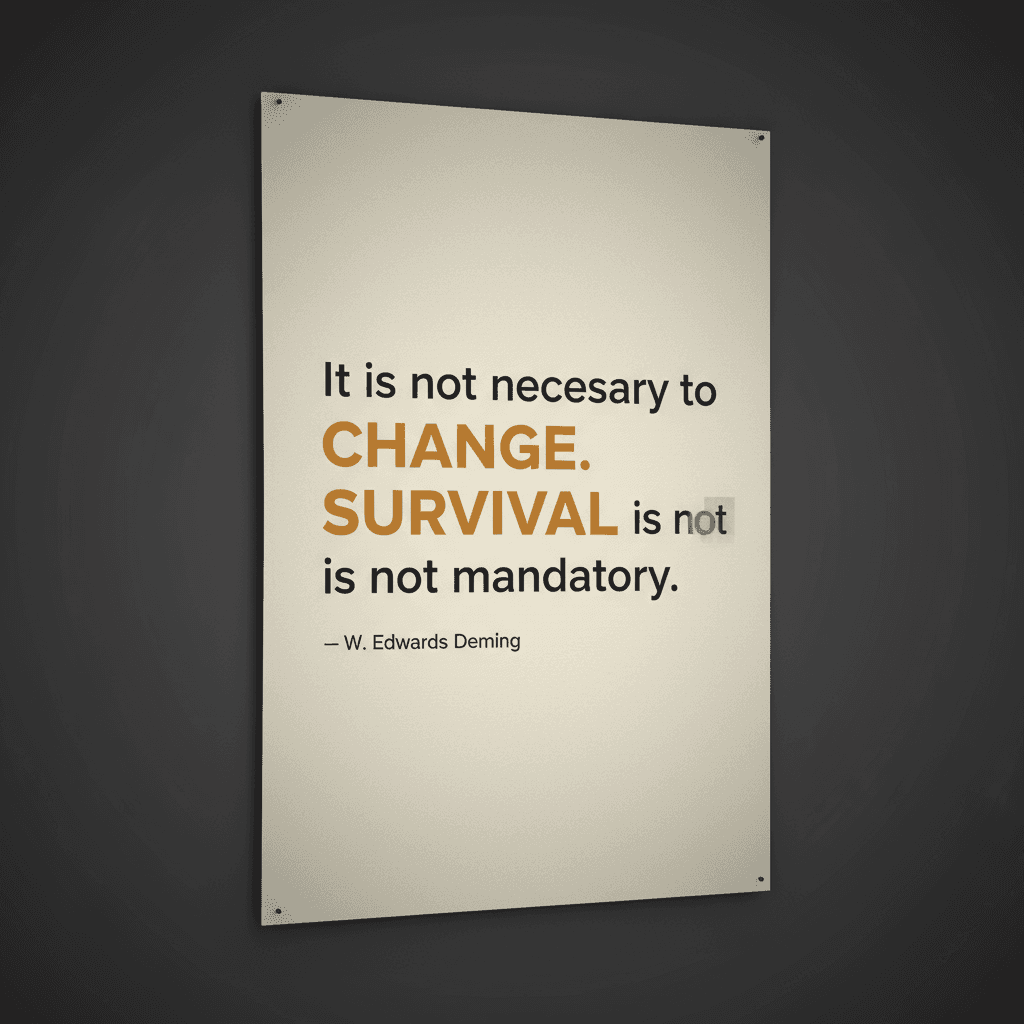改变不是必须的。生存也不是。 — W. Edwards Deming
命题的锋利与警示
这句箴言一针见血地把“自由选择”与“后果自负”并置:改变并非义务,谁都可以选择不变;但生存也从不保证,因此不变的代价可能是被淘汰。它并非煽动性的豪言,而是关于选择结构的冷事实——当环境的基线在移动,停留在原地就是一种隐性下注。由此,我们自然会追问:在怎样的情境里,不改变会直接威胁生存?
德明与质量革命的背景
顺着这个追问,德明的生平给出线索。二战后,他在日本推动统计过程控制与系统思维,通过JUSE讲座(1950起)强调变异管理与学习循环,后来在《走出危机》(1986)中总结“十四要点”与PDSA循环。其核心并非追求短期效率,而是让组织通过数据与实验持续对齐顾客与环境。这一背景说明,他并未鼓吹盲目革新,而是指出:当系统外部条件改变,维持旧设定等同于接受更高灭失风险。
历史回声:转型迟缓的代价
再看产业案例便更清晰。柯达工程师Steven Sasson早在1975年就做出第一台数码相机,但公司因路径依赖迟迟未拥抱数字化,最终市占崩塌。诺基亚在2007年iPhone出现后未及时完成从硬件到生态的迁移,优势迅速转弱。Blockbuster则在2000年前后错失与流媒体新范式的结合,终被Netflix超越。这些故事并非事后诸葛,而是提醒:当价值创造的“游戏规则”变更时,缓变即是变相的“放弃生存优先级”。
系统思维:为何改变是生存条件
因此问题不在“变不变”,而在系统如何因应环境变异。德明常说,绝大多数质量问题源自系统而非个人,被概括为“94/6”经验:若系统参数不匹配,再努力也抵不过结构性误差。当顾客需求、技术平台或监管规则迁移,旧流程与指标会放大偏差,形成负反馈的死循环。要想保住生存,就要主动重设系统边界与度量,使组织的学习与适应速度不低于外部变化速度。
用数据学习:PDSA与小步试验
接下来就落到方法上。德明倡导PDSA:计划、执行、研究、行动,以小步快跑验证假设,缩短认知半衰期。丰田生产方式的“现场改善”和安灯绳(大野耐一《丰田生产方式》, 1978)正是把即时反馈嵌入日常,让系统在低成本试错中更新知识。通过可视化指标、快速回路与跨职能协作,组织把“改变”从高风险豪赌,转化为连续、可控、可逆的学习过程。
何时不变:原则与边界
然而,并非一切都该改变。健壮的系统区分“策略可变”与“原则不变”:对安全、伦理、合规与顾客信任的底线不可动摇;对技术路径、组织结构与商业模式则保持弹性。药品质量标准、核安全规程等是稳态基石,而产品形态与交付机制应随证据更新。正是这种“硬边界+软策略”的设计,让改变服务于生存,而非消耗生存。
行动纲要:把选择变成系统
最后,把警句落实为日常工程:先定义生存相关的领先指标与阈值,再建立预警与复盘节律;以季度为单位运行PDSA组合,容许小败快速止损;把资源偏向能力建设而非短期产出,如数据基础、自动化测试与人才培养;将客户洞察嵌入决策闭环,确保每次调整都指向价值创造。如此,改变不再是被迫的跳崖,而是持续的攀登。